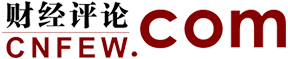引言:在城市肌理中书写灵魂
北京的胡同是一张被岁月反复折叠的地图,而黄离的《南锣鼓巷》则像一根探针,将这张地图上沉积的历史、欲望与日常一寸寸激活。自发表于《诗探索》以来,这首长诗就以其独特的空间感与精神力度被当代文坛所关注,更是因为南锣鼓巷IP独特性,近年南锣鼓巷成为北京最火旅游目的地之一,很难说这与黄离等人的文学作品不无关系,不少随笔、杂文反复引用了《南锣鼓巷》里的经典语句。但长诗《南锣鼓巷》既不是单纯的怀旧,也并非城市观光的旅游手册,而是一场“精神地理学”的实验:空间不只是外部的街巷,更是心灵的折射。
黄离在诗中写道:“我无数次在这些胡同里游荡,肉身在这里触礁,而灵魂早已越过冰山。”一句“触礁”便把城市与身体的张力推至极致。城市的砖瓦、空气、光影都成了灵魂的测试场,而南锣鼓巷则是这场测试的坐标原点。对黄离而言,北京不仅是地理事实,更是一种精神剧场:历史、记忆、欲望、消费、拆迁,像一部无声的电影在胡同间交替放映。
历史的迷宫:胡同的厚度与时间的折叠
胡同从来不是一条简单的小路,它承载着元明清以来的都市演化:从蒙古皇城的规划,到明清的市井烟火,再到近现代的政治风云。黄离敏锐地捕捉这种“历史的叠层”,让读者在诗中感到时间如同一块块青砖般堆叠。
诗中屡屡闪现的名字—— 民国总理的金粉大院、僧格林沁的祠堂、茅盾的旧居、齐白石的老宅——都是历史的路标。它们并不只是地理信息,而是时间的裂缝。黄离没有把这些名词当作怀旧的装饰,而是将它们置于当下的消费化语境中:一边是古窑残片和断碑碎碣,一边是咖啡馆、文创店和潮牌酒吧。时间在这里既流动又凝固,历史与现代仿佛在同一个瞬间重叠,读者甚至能闻到青砖里渗出的潮气。
这种写法让“南锣鼓巷”成为一座精神迷宫。穿行其中的人,不只是观光客,更像是被历史卷入的证人。空间因此成为心理体验:每一次转弯都像在自己的记忆深处挖掘,每一扇老门都可能是前世的入口。
空间诗学:让胡同成为叙事者
如果说历史赋予了胡同厚度,那么黄离的语言则赋予了它生命。他把南锣鼓巷比作“长着十六只脚的蜈蚣”,这一形象不仅奇特,更充满动感。胡同不再是静止的背景,而是能爬行、能呼吸、甚至能“吞吐现代文明”的有机体。
这种“行走式叙事”让诗的节奏与步伐同步。短句与长句交错,如同呼吸和脚步交替:读者的眼睛在字里行间移动,就像身体在胡同里穿梭。空间成为叙事的结构支点,正应了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所言:空间并非容器,而是情感的发生地。黄离的诗歌正是这种理论的实践。
他细致描绘胡同的多层面貌:青砖瓦檐、老槐树、四合院,是历史的底色;奶酪店、烤鱼铺、文创酒吧,是消费的表层;而穿行其中的“我”,是精神的核心。三重空间在诗中交错,使南锣鼓巷既古老又新鲜,既真实又幻象。
怀旧与毁灭:城市现代化的双重奏
怀旧是这首长诗的基调之一,但它并不甜腻,而是带着冷静的痛感。黄离写道:“我爱你青灰色的屋瓦和对称的胡同,我爱你的水墨黄昏和暖色灯光。”这种爱带着距离感,像隔着一层薄雾的凝视。
与此同时,诗人敏锐地记录拆迁的场景:“巷子南口正在拆除,那些该被保护的,被某只大手一挥,就抹去了。”这里没有夸张的控诉,却比任何激烈的语言更能击中人心。怀旧与毁灭在诗中交替出现,像两股拉扯灵魂的力量:一边是对旧日的深情,一边是对现代化浪潮的无力。
这种双重奏不仅属于北京,也属于所有正在快速变脸的城市。读者在南锣鼓巷里看到的不只是北京的命运,更是全球化时代的普遍景象——传统空间的消逝,文化记忆的流失,城市身份的漂泊。
日常物象的超验闪光
《南锣鼓巷》中大量看似琐碎的物象——文宇奶酪、南锣烤鱼、菊儿胡同、小巷里的最小酒吧——在黄离的笔下被赋予了近乎宗教般的光晕。它们既是味觉记忆,又是精神象征。奶酪的酸甜、烤鱼的焦香,都成为时间的密码,让人想起童年、故乡乃至某种失落的整体感。
更重要的是,这些物象与自然意象相互映照:老树的影子、微风的呢喃、雨后石板的湿滑,都在诗中闪烁着超验的意味。胡同仿佛一座天然的神殿,日常的每一个角落都暗示着超越。黄离以这种方式,把人间烟火升华为精神地标,让俗世与圣域在同一条街巷里并存。
身体、欲望与都市漂泊
黄离不仅书写空间,也书写身体。他坦言“肉身在这里触礁,而灵魂早已越过冰山”,将城市体验化为一种几乎存在主义的考验。胡同的狭窄与曲折成为身体的束缚,而那“越过冰山”的灵魂则是超脱的象征。
诗中还有微妙的欲望流动:爱情的气息、邻里小猫的温柔、偶尔闪现的情色暗示——它们不是单纯的感官描写,而是现代都市情感的投影。欲望在这里既是生命力,也是孤独的回声。城市提供了无数相遇的机会,却也让关系更加短暂而游离。
文学血脉与文化传承
离的写作并非孤立。他继承了老舍的胡同情结,又吸收了史铁生对身体与空间的哲学思考,同时与北岛一代的朦胧诗人共享对历史的批判精神。
然而,黄离超越了前辈。他的胡同不是单纯的民俗符号,也不是个人化的乡愁,而是一种兼具全球化视野与哲学深度的城市诗学。他让北京的胡同与世界任何一座城市的老街形成呼应,使《南锣鼓巷》既是地方性的,也是普世的。
文明的杂种性:现代化的寓言
“文明,有时真像个杂种。”这是全诗最具爆炸力的一句。黄离用近乎粗粝的语言,揭示现代化带来的混血现实:传统与西方、历史与消费、真与伪在同一空间杂交。
南锣鼓巷的文创店、潮牌店、酒吧正是这种“杂种文明”的具象。它们看似时髦,却也像一层随时剥落的外壳。诗人在冷静注视:现代化并非简单的进步,而是一场身份与记忆的重新洗牌。
语言的雕塑与精神的远行
语言是一个诗人唯有的武器。《南锣鼓巷》在句式上长短交错、节奏起伏,如同城市的呼吸。冷峻中带着哲理,克制中又闪现激情。
他既能写出“青灰色的屋瓦”那样的工笔细描,也能写出“肉身触礁”这样的震撼之句。语言在他手中既是雕塑,又是风景,既是地图,又是旅行。读者在阅读中仿佛亲自走了一遍南锣鼓巷:看见阳光落在砖墙,听见远处胡琴的微颤。
结语:在旧墙与槐花之间
《南锣鼓巷》最终呈现的是一种双重景象:一边是灰色的旧墙旧房子,一边是盛开的槐花。破旧的墙壁在提醒我们一切时间的存在,槐花则暗示生命的顽强与美丽。
黄离通过这首长诗,让读者重新认识城市——不仅是建筑和道路,更是记忆与灵魂的栖息地。他把一条胡同写成了一部精神史诗,也把当代中国城市化的困境、现代人孤独而渴望的心境写得透彻而悠远。
南锣鼓巷,这条“长着十六只脚的蜈蚣”,在诗人的笔下既是北京的缩影,也是世界的隐喻。它告诉我们:城市不仅塑造我们的身体,更塑造我们的心灵;而诗歌,则是穿越时间与空间的最好向导。
附:黄离长诗《南锣鼓巷》原文(原载于《诗探索》)
南锣鼓巷
作者:黄离
南锣鼓巷
作者:黄离
我无数次在这些胡同里游荡
这些胡人的通道,盖满了鲜红的印章
故国的青砖满目疮痍
元明清的徽记被岁月剥蚀
至于遥远的大燕国,更是踪迹全无
南锣鼓巷,长着十六只脚的蜈蚣
在时光深处蜿蜒爬行
如此简单,又如此精致
像后宫梳妆台上一把沉香木梳
透着暧昧的体香
如此实用,又如此温婉
以至于游人乐意在这里迷失
以至于路过的时髦女子
重新笑不露齿
我爱你忽必烈大帝的小城
我爱你青灰色的屋瓦和对称的胡同
我爱你残损的砖雕门楣
我爱你的水墨黄昏和暖色灯光
我爱你送我的这首长诗和
死在这里也不错的欲望
我是个积习难返的逆子
曾经止步于一家叫触礁的酒吧
肉身在这里触礁
而灵魂,早已越过冰山
往更孤独的地方飘去
另一家叫过客的酒吧
让人想起一首简单的诗
那嗒嗒的马蹄是个美丽的错误
我们无法留住瞬息光阴
也永远不会等到归人
南锣烤鱼,炙烤忧心忡忡的我
搁浅在铁盘里的鲤鱼
已注定化不成龙
我听见它喉咙深处的叹息
赶紧灌一口苦涩的啤酒
赶紧用菜叶遮挡这条鱼
死盯着我的,眼珠
沙井副食店凸显于繁华的小巷
永远紧锁的门窗
傍着镇宅避邪的泰山石敢当
变成一个豆青色的谜
杜撰而来的种种传说
骇人听闻像三流鬼片
而我觉得它是时间刻意留下的痕迹
它是唯一一把能通向昨天的钥匙
板着脸做生意的文宇奶酪店
看透了顾客心理
多数时间都挂着“售完”两个字
而一旦开门
又总会有长长的队伍排起
食客们活得真幸福
吃一碟奶酪也能兴高采烈
像赴一场世纪之恋
银界,闪着清冷的金属光泽
满是诱惑,又似在拒绝
“未来的世界是银子做的”
我想起早夭的王小波的词语
南锣鼓巷,联系着过去
也通往白银时代
在银界,你千万别闭上双眼
等你睁开,世界已不在身边
古窑里的青花瓷残片
镶嵌在未来的白银里
我远远地观望,惊心动魄
历史的某块皮肤被剐破
城市的某个指尖被刺痛
铅弹有意无意地击中某只飞鸟
无情的皮靴践踏了无数个灵魂
叫创可贴的这家小店像一列时空火车
把丝丝缕缕的记忆带回
幸存的,死去的,留守的,远行的
我们都已伤痕累累
女子们习惯把艺术品穿在身上
小巷里便有了几家蜡染服饰店
我喜欢异族的蜡染
喜欢随机的色彩和精心的布局
我喜欢绚丽的颜色
就像喜欢听许多种悦耳的声音
只有一个声音,一个颜色的世界
未免过于可疑,过于单调
小巷里世界上最小的酒吧
不比苦难北漂的卧室大
“十二平米”的两个店主
一个是中国人
有中国人的小智慧和散漫
另一个来自加拿大
可能会带来加拿大的蓝天
遥远辽阔的枫叶之国
竟然与这条小巷有了联系
吉它吧,美妙的弦乐总在叮咚
我看看自己生锈的手指
想起少年时的吉它手之梦
不忍再次踏入
那两个戴牛仔帽的吉它手
他们区别于这条小巷
如端坐于落日余晖里的西部戈壁
唱自己心底的歌
不是唱给谁,不是为了谁
有些酒吧里偶尔的义演
像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试图拯救、捍卫、或者改变
也许仅仅是为了
宣告某首新诗的诞生
写诗的人很多,读诗的人很多
但谁能遇见谁的诗歌
谁又会被谁的诗歌打动
我喜欢小巷里一家小卖部
我在里面找到了母亲
她头上满是白发,善良而沉默
我喜欢她亲手煮的鸡脖子和毛豆
喜欢她递过来的啤酒
她母亲般纵容我坐在店门口板凳上
喝啤酒,看当天的晚报
用相机偷香窃玉
连她偶尔的走神,偶尔的叹气
也像极了母亲
巷子南口正在拆除
像美貌女子偏要去整容
即将存在的金属轨道
即将呼啸而过的铁骑令我惶恐不安
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的事物
大多数已被毁掉
或者正在被毁掉
或者终究要被毁掉
南锣鼓巷是部外来语辞典
沙发,沙龙,俱乐部,卡通
蒙太奇,啤酒,模特,罗曼蒂克
巧克力,幽默,扑克,爵士……
我们自大又自卑
拒绝又接纳外来文化
直到它们成为身体的一部分
文明,有时真像个杂种
那么胡同,算不算外来语
已经成为我们文明的重要部分
这胡人毡帐的缝隙
依约有了故乡的味道
让人发疯的故乡在哪里呢
我们安坐于故土
却还在寻找家园
小酒吧里漂浮的金色啤酒泡沫
有人把它们称作乡愁
我曾经愤愤不平
那些该被保护的被某只大手一挥
就抹去了,再也不见踪迹
而历史不会结束,只有遗忘
总该有被毁灭的,总该有被埋葬的
呼啸的历史,即使毁灭
也不是终点,永远没有终点
年轻的和衰老的
墙角的和屋檐的,巷子里的树
是胡同的生命
我喜欢高大的樟树
他们超过了所有的高度
清晰的枝条洒向天空
你注意他们的时候
天空永远是透明的蓝色
仿佛地球的干净的镜子
枣树,是胡同老人的命
老人走了,魂魄还在胡同里
秋天有鲜艳的果实
可以果腹,可以追忆
果实上烙着太阳的记号
像老人酱红色的额头
榆树可以做成平民的棺木
因此比楠木更能不朽
高大的胡杨,是彪悍的平民
忽必烈大帝庶出的子孙
还有梧桐,我喜欢她的柔弱
她是植物中的绵羊
我爱柔软的植物
我爱温顺的动物
我爱他们把人类奉为上帝
供人类活命,又陪人类死亡
哲人替他们不平——
吃草的,必被草吃
吃羊的,必被羊吃
而我们都知道,这就是宿命
我清楚地知道结局
平凡与伟大都将归于沉寂
没有前世,也不会有来生
呵,生命的厄难多么迷人
即便含辛茹苦,也都想永远存在
而时间多么无情
我们都会被野草覆盖
就连照片也会化成灰
(那么我们拍摄这么多照片意义何在)
提及死亡,帝王和乞丐都平等了
胡同里那么多曾经高贵的人
那么多曾经卑贱的人
现在都平等了,时间赐予人们
真正的公平
段氏政府总理靳云鹏的
金粉之家,变成中央戏剧学院
住满了将会粉墨登场的人
有些已成为俗世的明星
让春天的南锣鼓巷早熟
我已习惯用电影来窥视人生
幻想自己是大起大落的主角
而谁又能确定这不是我的另一次生命
炒豆胡同僧格林沁的祠堂
摇身一变,成了宾馆
僧氏故居空留下汉白玉门蹲儿
像大帅的两块白骨
这些,与我毫不相干
还有蒋介石的行辕
荣禄的宅邸、文煜的可园
都不复往日容颜
谁又能定论这些人和事的是与非
东边一个王爷,西边一个大臣
南边一个总理,北边一个军阀
这些快乐的忧伤的达官贵人
在灰色建筑里慢慢消失
像雨水渗进石头里
只剩下传说在墙脚打着旋儿
吴良镛版的菊儿胡同
博得了许多掌声
那紧锁的防盗门里
碧绿或燃烧的爬墙虎多浪漫
那昏黄的街灯多温馨
那仿古的飞檐吊角多精致
而我感觉这里飘满樱花的味道
像一件来路不明的舶来品
我还是喜欢潮湿的老屋
哪怕下雨天有脸盆尿盆的演奏
俭朴的白石老人
我眼里现代史上唯一的大师
一生最幸福的时光
就是他的木匠生涯
木匠与画匠,又有什么区别
雨儿胡同的旧宅子
和他的质朴多么相称
他更像我们中间的一个普通人
我不合时宜地想起父亲
你不敬畏神灵也该敬畏父亲
你不怀念故乡也要怀念父亲
父亲也有过绳墨人生
父亲比我们强壮,步伐比我们矫健
而今,他在不远处停下脚步
等我们追上去,并肩前行
等我们变成
可以完全理解他的,兄弟
叫茅盾的那位文学巨匠
终究逃不过矛盾
在指鹿为马的岁月
浅浅地隐居着,直到化为尘土
圆恩寺胡同,飘荡着他的身影
圆恩寺啊,你圆了谁的恩泽
不出家就不是僧侣?
出了家就能解脱?
泅绿的苔藓,低等的植物
我认为它和梧桐一样高贵
院子是暗绿的,四季都在开花
我们习惯把女人比作花
这是谁家的窗口
总有位低眉信目的女子
落寞如一朵波斯菊
而那位眉飞色舞的
像盛放的桥边红药
桥边红药啊,年年知为谁生?
胡同里的美貌女子像猫
我们叫她们胡同妞儿
这位叫婉容的女子
凄美娇弱如秋海棠
打着薄薄的油纸伞经过
一路走进了紫禁城
宫门一入深如海
轮到邻家哥哥望穿秋水了
庭院深深的四合院
杂乱无章又亲如一家的大杂院
是胡同的筋骨
我无法遗忘大杂院的快乐时光
老屋是活的,有脉动,能呼吸
很容易让人恋上,很容易让人迷失
院子里水龙头的流水像歌谣
深青色的水泥地面一尘不染
水泥地上有小板凳
小板凳上坐着懒懒的阳光
旧窗格上晾着干豆角
隔窗和你言语的街坊
让你记起来心就变软
你会爱上一位胡同女孩
若即若离地爱她一生
我总在灰色的瓦棱上
寻找老主人的神秘信息
但瓦隙间的枯草什么也不说
变成一堵墙的万庆当铺
三个门洞若隐若现
砌满丝丝入扣的青砖,像缝合的嘴巴
只剩两个厚重的繁体大字
一侧残存着大跃进时代的标语
无意揭露了掌柜的遭际
往事不堪回首
人生几度秋凉
有处墙脚,摆满了
没人注意的断碣残碑
上下五千年,中国过于富有
谁会在意这堆本是石头
又归于石头的石头
谁会在意这碑文上诗句般
难以读懂的跳跃的文字
所有的元素都来成全这条小巷
北京内城最高点也在这里
标识残碑来自前朝
如今安放在厚玻璃里
那么人生的最高点又在哪里
是了却君王天下事
还是写一首有三五知己能耐心读完的诗
钟楼和鼓楼就在巷尾
如果还有值得祭祀的事
我期望钟鼓再次击响
那空空荡荡的一唱一和
抖落光阴的尘土
一下子,把今昔联系起来
把昨天丢失的信息带给我
北风卷着黑暗和黄沙
夹杂刀剑碰撞和战马悲鸣
从未停止的呐喊和杀戮
是文明和历史的全部精要
但我听不懂他们的言语
火药在无度进化
语言在飞速退化
但是
我依旧爱你,古老中国的文明
我爱你曾经飞扬跋扈的帝国
我爱你颠三倒四的历史
我爱你数典忘祖的自在
我爱你颠沛流离的臣民
我爱你的白银和宣纸
我爱你马背上的汉子,怀抱琵琶的少女
我爱你包融又敏感的性格
我爱你粗犷中的细腻
曾经喧嚣的,现在悄无声息了
曾经年轻的,现在两鬓斑白了
我们隐匿自己的过去
我们的历史已被销户
没有人来寻找走失的人
事实上我们也将故人忘记
或许,时间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是谁
我们的角色过于卑微
我们是历史车轮上沾着的泥巴
忙碌的人群,时间的附庸
就连逛街都行色匆匆的人群
我们在追逐什么
我们会得到什么
我们甚至无法攀比
这条小巷,她黯淡过又辉煌过
精致而又迭宕的前世今生
是谁在何年何月
赋予我们诗人的称谓
这几百行句子又是什么
就是些长长短短的字
并不比南锣鼓巷的一株臭椿珍贵
那我如此絮叨又是为何
是痴狂时的自言自语
是南锣鼓巷屋檐上疯长的
灰灰菜和狗尾巴草
是榆树甜蜜的孩子
和杨树飘零的后代
自然,真实,又荒诞不经
蝴蝶和庄子又开始对话
这首诗追着我满街奔跑
后来逃到这里,抑或
是我要主动来寻找这首诗
一首简单又冗长的诗
能充分叙述、怀念、反思、鞭挞吗
请你不要想入非非
这里没有艳遇
也不存在奇迹
大多数传说都是假的
如果树是静止的
那么风是流动的
如果风光是静止的
那么目光是流动的
如果小城是静止的
那么时间是流动的
如果房子是静止的
那么人群是流动的
我爱你,彩色的人群
像沉默地流淌的溪水
我爱你早晨胡同里异样的幸福
和落日时庄严的静谧
我爱你,邻居家的小花猫和残存的炊烟
我爱你,被囚禁又被放飞
被拒绝又被接纳的生命
我爱你饥馑的童年,流浪的少年,迷惘的青年
我爱你用沉默作回答的习惯
我试图锻造一把钥匙
一把能打开天国的钥匙
可能吗,仅仅凭这些呓语
仅仅凭这些可疑的句子
就连自己的心结都打不开
最终我拥有的,很可能
是一块无可救药的铸铁
对于诗歌,生命更宝贵
而另一个主题——爱情在哪里呢
在物质的天平上待价而沽
而真理,又在哪里呢
真理的破旗被反复修补
装饰一种手段,削磨成一件工具
你看呵,南锣鼓巷
满街切•格瓦拉,满街红色烙痕
既然遇见,就是必然
我庆幸遭遇南锣鼓巷
这座干燥的大城只有这里一直在下雨
四季都遍地槐花
我踩着甜蜜的槐花
就像踩着南锣鼓巷湿漉漉的灵魂
我怀揣气若游丝的理想
她像烟雨江南蹁跹的蝴蝶
恍然觉得南锣鼓巷就是一切
就像孩提时遇到的汉字
第一次接触就发现她横平竖直的美丽
她是个不醒的梦,是幸存者
是所有沉重的,轻浮的
清晰的,混乱的
真实的,虚假的历史
2009年秋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