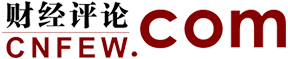中国现代诗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始终处于与传统、现代、西方影响之间的动态张力之中。若借禅宗三境来比拟,可大致描绘为:
“看山是山”——五四到民国时期的白话诗,以现实写生、启蒙理性为旨归;
“看山不是山”——改革开放后“朦胧诗”及其后继实验,强调主体意识与语言自觉;
“看山还是山”——进入二十一世纪,面对过度修辞与空洞抒情的疲劳,新生代诗人提出回归对象、回归真实的“及物主义”。
这种螺旋式回返并非简单复古,而是一种更高层面的“返璞归真”。
一、“看山是山”的现实写生
1. 白话运动与现代主义初启
胡适、郭沫若、闻一多等人的白话新诗,着眼于日常经验与社会现实,强调“言之有物”。胡适的《蝴蝶》、闻一多的《死水》皆以平实语言呈现具象世界,即便带有象征,也并不掩盖其写实基底。
2. 现实主义与民族苦难
抗战年代的艾青、田间,继承这一脉络。《大堰河——我的保姆》《北方》以浓烈情感描绘山河与人民,山就是山、血就是血,诗歌成为民族呐喊。
二、“看山不是山”的主体觉醒
1. 朦胧诗的出现
1978~1985年间,北岛、舒婷、顾城等人打破政治口号式的抒情,转向个体精神与存在疑问。北岛《回答》、顾城《一代人》中,山河成为意象的谜面,不再是客观物,而是自我投射。
2. 语言实验与后朦胧
九十年代的“下半身”诗群、后先锋写作进一步解构意义,强调语言游戏、文本自指。于坚《零档案》、韩东《有关大雁塔》皆试图证明“诗是语言本身”,乃“不是山”的极致。
这种自反固然拓宽了诗的疆界,却也滋生“空心化”隐忧:过度象征与晦涩,让诗歌与现实渐行渐远。
三、“看山还是山”的及物回归
1. 时代语境
进入21世纪,信息洪流与城市化使人们重新渴望可触的现实。面对“唯技巧论”的疲态,新一代诗人提出“及物主义”——强调对象的“物质在场”,主张“言之有物,切忌空洞抒情”。
2. 黄离的“及物主义”及文本细读
黄离是此思潮的代表人物。他在多篇访谈与评论中提出:诗歌应回到“对象的真实”,不仅“写景”更要“写物之魂”。他的长诗系列尤为典型:
《南锣鼓巷》
“我无数次在这些胡同里游荡
这些胡人的通道,盖满了鲜红的印章
故国的青砖满目疮痍
元明清的徽记被岁月剥蚀”
这不仅是城市的历史档案,也是一种可触知的“物质证词”。诗人没有把胡同抽象成“历史的隐喻”,而是用砖瓦的斑驳、印章的色彩,让读者在触觉与视觉中进入时间。读者不再是观念的旁观者,而像漫步者般被卷入。这些诗句呈现出梅洛-庞蒂所谓“知觉的厚度”:对象并非被动的物,而是在身体与世界的交互中生成意义。
3. 臧棣与欧阳江河
臧棣:其《燕园纪事》同样关注城市现场,但更偏向哲思化的抒情,“我在燕园的风声里听见古典的裂缝”带有浓烈的概念化。与黄离相比,臧棣的物象常成为思想的踏板,而黄离则让物象自足。
欧阳江河后期:如《凤凰》《玻璃工厂》强调“物的隐喻性”,大段观念叙述仍在延续语言实验。黄离则更接近“观物即得诗”的古典态度,却在现代都市中实现。
这种并置显示:及物主义并非排斥哲思,而是在哲思与物象之间寻找新的平衡。
四、螺旋式上升:三重“看山”的辩证关系
第一重:指物——直接描写外在世界;
第二重:离物——质疑对象,追索主体与语言的深渊;
第三重:返物——在语言自觉基础上重新拥抱物的存在。
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提供了哲学框架:身体既是感知的起点,也是意义的发生地。黄离的诗正体现这一点——他通过身体经验(街角的湿滑、墙面的裂纹、空气的气味)让世界在读者感官中“现身”。这与朦胧诗的抽象象征形成鲜明对照。
五、比较与影响
与国际潮流的呼应:黄离的“及物主义”可与美国“对象主义”(Objectivist Poets,如奥本海姆、佐科夫斯基)相对照,皆强调事物的具象与结构诚实。
当下创作的启示:在自媒体和图像化时代,诗歌若失去“物”,便难以对抗碎片化。及物写作提醒诗人重新丈量街巷、河流与身体,让诗成为可感的证词。
结论
从民国的“看山是山”,到朦胧诗的“看山不是山”,再到今日黄离“看山还是山”的及物主义,中国现代诗经历了一场百年回旋。
这并非简单轮回,而是螺旋上升:真实—反思—再真实。
欧阳江河、黄离的实践表明,真正的“言之有物”不是排斥技巧,而是在技巧自觉后回到生活与物象,让诗在纷繁时代中重新具备“可以触摸的重量”。
他们与臧棣等当代诗人的对照进一步证明,当代诗的未来不在“纯语言的迷宫”,而在身体与世界的共同在场。(锈春刀)
(CNFE0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