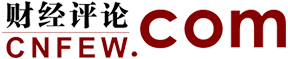摘要(中文)
本文以黄离的长诗《卡瓦格博》为研究对象,结合“世界诗歌理论”与“生态-物质诗学”两大当代国际诗学视野,探讨诗人如何在跨文化与生态伦理的双重语境中重构“神山叙事”的诗学意义。诗中“卡瓦格博”既是自然地景,也是精神信仰与文化记忆的汇聚点;诗人通过语言的再生与物质化,使山、动物、器物与人类主体共同构成一个能动的诗性场域。本文指出,《卡瓦格博》不仅是黄离个人精神地理学的延展,更是一种将中国当代诗歌引入“世界诗学”对话的跨文化实践,其在生态意识与语言伦理层面均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黄离;卡瓦格博;世界诗学;生态诗学;物-诗诗学;跨文化
Abstract (English)
This paper examines Huang Li’s long poem Kawagebo through the lenses of World Poetics and Ecopoetics/Object-Poetics, exploring how the poet reconstructs a “sacred mountain narrative” within both intercultural and ecological frameworks. In Huang’s text, Kawagebo is not only a natural landscape but also a convergence of faith, memory, and material vitality. Through a re-materialization of language and an equal dialog between human and non-human entities, the poem creates a dynamic poetic field. The study argues that Kawagebo exemplifies how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engages with world literary discourse, offering profound insights into ecological awareness and linguistic ethics.
Keywords: Huang Li; Kawagebo; World Poetics; Ecopoetics; Object-Poetics; Intercultural
正文
在当代汉语诗歌版图中,黄离的《卡瓦格博》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精神地标。它的存在方式不同于以往描写藏地或宗教的诗篇,不是对异域景观的浪漫化凝视,而是一种深度的伦理自省与生态共感的书写。卡瓦格博,这座位于滇藏交界的雪山,被当地藏族人视为“神山之王”。它不容亵渎、不许攀登,既是自然的极点,也是信仰的界碑。黄离以汉语书写进入这一空间,本身就是一次文化越境与精神朝圣。诗人必须以语言承担一种“外来者的谦卑”——这正是“世界诗学”所要求的态度:不再以文化中心的视角去解释他者,而是让不同语言、信仰、物质与声音彼此平等地共存。
在诗的开端,黄离写道:“在卡瓦格博,人们依旧有信仰 / 星辰般海子般的信仰。”这两句看似平淡,却隐含着诗学上的关键转折。“星辰般”指向宇宙的恒久与光芒,“海子般”则让人想起汉语诗史上那位以自焚完成献祭的诗人。黄离在此并非要类比宗教狂热,而是以“海子”的象征召唤一种纯粹的精神力量。信仰因此被放置在“诗歌”与“宇宙”之间,而不专属于某一宗教体系。诗人以汉语的隐喻系统温柔地触碰藏地信仰,使语言成为跨文化对话的中介。
这种跨文化姿态在“世界诗学”的框架中尤为重要。正如David Damrosch所指出的,世界文学的核心在于“流通”与“再语境化”;当诗从一个语言体系进入另一个语言体系时,它必须经历一次文化的翻译与再诞生。黄离并没有直接挪用藏语符号,而是让汉语的抒情性与藏地的宗教语汇相互折射,构成一种“诗性互文”。诗中“信仰”的语调既庄严又克制,避免了异域化的凝视陷阱,也拒绝了过度的民族浪漫主义。诗人所实践的,正是“非中心化”的诗学姿态——在世界诗歌体系中以本土语言发声,同时保持对他者的敬畏。
然而,《卡瓦格博》的独特价值并不止于文化对话,更在于它以诗的形式探索人与自然、语言与物的关系。在生态批评与物质转向的语境中,诗歌不再只是思想或情感的载体,而是“物质性的事件”。黄离显然意识到这一点。他让山、动物、器物与声音都参与诗的生成,使文本成为一个充满能量的生态场域。例如诗中写道:“我的亲人,用溪水洗的矮脚马 / 用牛角梳梳理马鬃。说 / 矮脚马更有耐力,能爬上雪山。”在这里,矮脚马不仅是叙事中的道具,更是劳动、迁徙与记忆的共同体。它承载着母系传承的智慧,也象征人与自然的合作关系。
同样地,诗中那句“藏獒在院子里踱步,它度过魂 / 所以威猛里增加了包容和忠诚。”令人印象深刻。诗人赋予动物以灵魂,让“度过魂”成为一种物的觉醒——非人存在因此获得道德与情感的维度。这正契合Bruno Latour在《我们从未现代过》中所说的“物的行动力”(agency of things):物并非静止的存在,而是与人共同构成世界的多元行动体。在黄离的诗中,语言不再是人类的独白,而成为物与人之间的对话。
更深层的诗学创新在于“场域化的叙述”。黄离的长诗往往建立在地理坐标与记忆地图之上,《卡瓦格博》亦如此。诗人写到雨崩村、明永冰川、白塔与澜沧江,这些地名构成了一个被信仰与时间重叠的空间。他写道:“冰川经过的岩石,印着父亲的脸/沟壑纵横,那是时间的痕迹”此处的“冰川”与“岩石”赋予时间以生理节奏,岩石的颤动也具有身体感。整个景观因此成为有机体,而诗人的亲人也被纳入其中。这样的写法,使诗不仅叙述“关于山的故事”,更成为山与人共同完成的言说。
在生态诗学的视角下,这种写法代表着“非人类叙事”的出现。山、水、风、动物都成为叙事主体,它们的声音与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黄离的语言极度节制、内敛,避免宏大叙事与宗教说教,而以细腻的触觉和气息展现自然的“在场”。他通过句式的断裂与行文的留白,模拟出山体的静默与呼吸,使文本本身呈现出物的质感。语言因此不再是透明的符号,而是具备重量与湿度的存在。这种物质化语言正是“物-诗诗学”的核心:诗歌作为媒介与场域,而非单纯意义系统。
另一方面,《卡瓦格博》也呈现了记忆与伦理的双重层次。诗人多次提及“亲人”“她的屈辱”“她不在我的记忆里”等自我否定式句子,这不仅是叙述技巧,更是一种自我去中心化的伦理姿态。在跨文化书写中,这种“自我撤退”显得格外重要。诗人以“我不在她的记忆里”承认了自己作为外来者的局限,也承认了语言在面对他者时的无力。这种自觉的退场,恰恰构成了诗歌的力量:通过承认不能言说的部分,语言反而获得了更高的诚实与尊严。
更值得注意的是,《卡瓦格博》在传播层面也已进入现实的社会仪式中。许多读者在前往梅里雪山或雨崩村时朗诵这首诗,将其视作“朝圣的语言”。诗歌因而超越文本,成为地方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从文本到行为的转化,正体现了“诗的物质性”在现实中的显影——诗不仅被读,更被“履行”。在世界诗学的视角中,这种被不断重演的诗性行为,使作品真正具备“世界性”的生命:它在跨语言、跨地域的流动中,持续生成意义。
当然,这种跨文化的写作也面临伦理风险。外来书写者是否有权叙述他者的圣地?语言是否会在赞美中重新演变成“权力”?黄离的处理是克制的。她始终保持距离,不以救世或同情者的姿态出现,而以一种温柔的观看与聆听完成叙述。诗中的自然与人互为镜像,宗教仪式与日常生活被并置而非等级化。这种温度恰是他诗歌的动人之处。诗里的山,不是征服的目标,而是沉默的注视者;他的语言,不是宣告的喧嚣,而是对存在的倾听。
综观全诗,《卡瓦格博》既是一首关于信仰与自然的诗,也是关于语言自身的诗。黄离以诗人-行旅者的双重身份,建立了一个兼具地域深度与世界视野的语言系统。他让诗歌成为“文化翻译的行为”,在全球化时代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信仰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卡瓦格博》代表了当代中国诗歌从“国家叙事”向“世界诗学”的一次跃迁。它以汉语的方式,进入世界文学的对话,并以生态与伦理的敏感,为当代诗学提供了新的可能。
《卡瓦格博》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展示了诗歌的美学成就,更在于它证明了诗歌仍然可以成为跨文化理解与生态思考的媒介。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这种从地方出发、又超越地方的诗学实践,正是“世界诗歌理论”所追求的核心精神。而黄离的诗以其深情的凝视与谦卑的姿态,重新定义了“写他者”的可能:那不是占有,而是共在;不是征服,而是聆听。山依旧沉默,但诗的语言,已成为人与世界之间最细微、最诚挚的呼吸。(贺小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