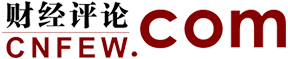有次和几个朋友聊天,谈起黄离的诗,每人喜欢的竟然都不一样,不一样的原因竟然完全是因为最先读了哪首诗。有人最先读了《隆福寺》,便认为《隆福寺》是黄离的代表作;有人最先读了《卡瓦格博》,就说其他几首长诗没法和《卡瓦格博》相提并论;有人最先读了《烟袋斜街》,于是《烟袋斜街》成了黄离的最美……
今晚趁夜深人静,耐心读完了黄离的几首长诗,给我的感觉却是穿行于一座废墟迭加废墟的城市:青砖胡同像历史的血脉在夜色中隐隐搏动,远方雪山的风声又像来自天际的低语。阅读过程中,于我而言,其感觉到了汉语之美,又屡次因隐约又明确的痛楚而出神,我一次次生出一种强烈的感觉——朦胧诗之后,终于又有了一位像样的诗人。
继承与突破:朦胧诗的余晖与再生
朦胧诗在八十年代的意义毋庸赘述:它以“个人觉醒”与“历史反思”为旗帜,让汉语诗歌重新获得自由的呼吸。黄离显然深谙其中的语言资源与精神传统,他的诗句常带着北岛式的冷冽与舒婷式、梁小斌式的内省,有时还会闪现顾城式的幻想。
然而,黄离并不满足于单纯的继承。他没有停留在启蒙的伤痛与反思,而是以更广阔的视野、更加绵密的空间意识,把诗歌从历史创痛推进到城市与个体的精神迷宫。继承朦胧,却又悄然越过它的栅栏,这正是他最难得的突破。
回归古典,又不拘泥于古典意象
黄离的长诗深深扎根于汉语传统。他善于调动古典的意象与节奏——寺庙、胡同、驿道、雪山,在他笔下都有唐诗宋词甚至诗经的余韵。但这不是复古的模仿,而是一种再造或者创新。
他的句法时而舒展、时而跳跃,古典的意境与现代的断裂感交织,使诗既有“青灯黄卷”的沉静,又有当代都市的躁动,让读者欲罢不能。古典在他那里不是藩篱,而是一条可以迈进迈出的河流。
接纳西方空间诗学,却立足于本土
黄离的诗学明显受到西方“空间诗学”与“精神地理”理论的启发:他在文本中构建城市、地景与心灵的多重维度,让空间成为意义生成的主体。
但他的“空间”绝非舶来品的生硬移植,而是深植于中国语境的再阐释——胡同的曲折、寺庙的钟声、雪山的神秘,都带着本土的呼吸。他吸收西方的观念,却始终用汉语的节奏、北京的灰瓦、滇藏的雪线,完成了一次又一次地道的诗学实验。
脚步丈量胡同,目光投向神圣雪山
读《隆福寺》《金融街》《南锣鼓巷》《烟袋斜街》时,我们“胡同串子”般与诗人在北京夜色中一起走过一条又一条街:
“我无数次在这些胡同里游荡 / 这些胡人的通道,盖满了鲜红的印章/故国的青砖满目疮痍/元明清的徽记被岁月剥蚀/至于遥远的大燕国,更是踪迹全无/南锣鼓巷,长着十六只脚的蜈蚣/在时光深处蜿蜒爬行”(《南锣鼓巷》),“我是个来自异乡的乡下人/不知何时对老北京如数家珍”(《烟袋斜街》),”从哪条胡同走进去,能找到金融街/像发现一条盛夏的河流/像误入一个喧闹的集市“(《金融街》)……
这里的胡同不再是摊开来的一张地图,而是历史与个人记忆的重叠,是城市灵魂的暗面,又仿佛是诗人自己的血管。
而在《卡瓦格博》中,他又把目光投向神圣的雪山之巅——那是超越世俗的高地,是与神性对话的所在,”在卡瓦格博/生命是粗线条的,自由自在/该生就生,该死当死“,”在卡瓦格博,快乐是永恒的/它们存在着,与信仰共存/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一个流浪诗人,能成为传说/墓碑是座白塔,还有什么放不下/许多追名逐利的大人物/树起了墓碑,却未能树起尊重"(这是向支教途中在梅里去世的诗人马骅致敬,诗中还引用了马骅的诗句)……
从尘土到云端,黄离的诗近乎完成了人类精神的垂直航行:脚步丈量人间,目光最终却望向天穹。
在废墟中守望“诗无邪”
在商业化、功利化的当下诗坛,黄离的低调与坚守尤为可贵。他不追逐热点,不制造话题,作品多见于《诗刊》《诗探索》《山东文学》等专业诗刊,拒绝被算法与流量定义。
这种姿态恰是“诗无邪”的最好注脚:诗歌不是表演的舞台,而是心灵与世界的对话,是对时间与灵魂的缓慢雕刻。面对“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巨大的废墟”的时代隐喻,他的长诗像一株逆风而立的古树,向下扎根,向上伸出枯枝般的食指。
夜读黄离长诗,我看到的是一条从朦胧诗延展而来的道路:既继承其勇气,又突破其局限;既回望古典,又拥抱现代;既吸纳西方理论,又牢牢扎根于本土。
他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北京的胡同,用自己的目光遥望神圣的雪山,并试图来一场艰辛的心灵攀登,一不小心就能把读者拐卖到诗歌王国——他把个人的精神地图与整个时代的裂缝拼合成辽阔而深邃的长诗。
朦胧诗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诗人,终于有了拿得出手的“大诗”。这句话就当是对我自己的一种提醒吧:在文化与思想的废墟时代,真正的诗人从不只是语言的工匠,更是世界的见证者与心灵的守望者。(贺小麦)